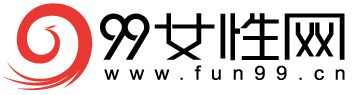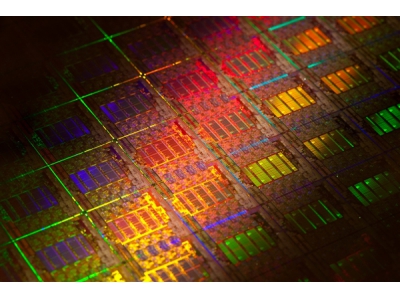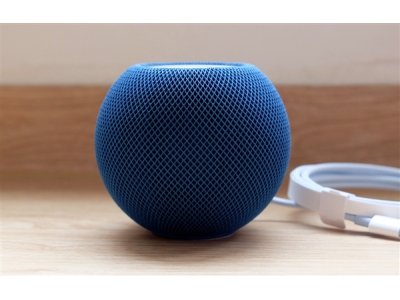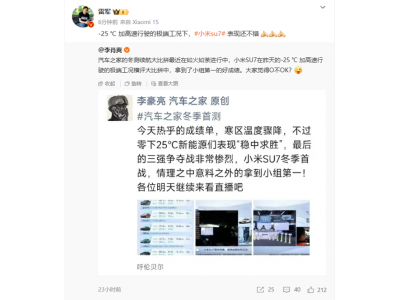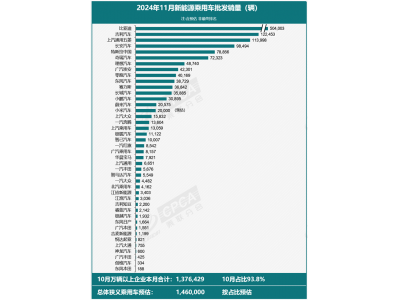揭秘物种进化:那些毫无用处的痕迹器官
扫一扫
分享文章到微信

扫一扫
关注99科技网微信公众号
原标题:揭秘物种进化:那些毫无用处的痕迹器官
利维坦按:英文中的“evolution”一词现在大多翻译成“进化”,只是这词原本用来指代事物的变化与发展,到了19世纪才开始衍化出“进步、高级化”的意义。
然而生物演化不存在进步退步的分别,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第一版《物种起源》的时候,也只在结尾段中用到了“evolution”一次。与之相比,达尔文更倾向用“发生了改变的继承(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)”等词组来替代我们所说的“进化”。
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相关中文译法上。对于“evolution”一直有两种中文翻译:一是“进化”,源自日制汉语“進化”;二是“演化”,与严复在《天演论》中所用的“天演”一词相近。
严复半著半译的《天演论》源自赫胥黎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,书中借进化论所倡导的“优胜劣汰”观点无疑加速了大清的灭亡。
同样的,中文语境中“进化“一词也有生物从低级到高级,由简单到复杂的描述成分,同时还有反义词“退化”。矛盾的是,所谓退化也只是进化的一个形式。而“演化”一词则否认了生物发展的方向性,因此更为适用于在生物学上的讨论——即便本文所讨论的大致上还是“退化”这件事。
从早期猿人到现如今,人类只走过了大概20万年。虽然相对于地球40亿年的发展来说,这压根不算什么——但即便如此,人类还是经由20万年的演化终成光溜溜的模样,有些器官也因为不再派得上用场而发生“退化”。

对于现代人来说,它们依然会向我们揭示人类自己曾经的模样。因此我们赋予这些失去功能,在发育中退化,只留残迹的器官一个略显悲壮的名字——痕迹器官。
早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观点之前,前人就已经屡次发现生物的退化结构。比如说,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就提出观点,认为鼹鼠的眼睛是“发育受阻(stunted in development,成年鼹鼠的眼睛只能用来感受白昼与黑夜)”。
由于长期生活在地下,鼹鼠的眼睛已经完全退化。
而德国解剖学家罗伯特·维德斯海姆(Robert Wiedersheim)在1893年出版的《人的结构》(The Structure of Man)一书中,更是列举了86个呈现出退化性的人体结构,虽然其中包括胸腺等当时人们还没意识到其作用的重要结构,但这个名单在后期更是扩大到了180个。
但是一直到上世纪中叶,我们才敢割去阑尾。
阑尾,这是一个从小听到大、但从来没亲眼见过的器官,据说位于盲肠根部,在人类进化早期可能起到消化粗纤维的作用,随着人类饮食结构的升级慢慢退化,但是食草动物的阑尾却依旧十分发达。
美国生理学教授劳伦·马丁在2007年研究发现:阑尾在胎儿时期就开始向肠道提供免疫用的淋巴细胞,在20-30岁的时候淋巴细胞数量会达到最高峰,是很重要的免疫器官。
但是在早年间,由于医学界对于阑尾的积极作用了解相对片面,认为这只是进化过程中留下来的一段毫无作用的肠子,加上阑尾炎的发作多为急性,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棘手的炎性肿块,甚至威胁生命,因此大多采用切除阑尾的手术办法进行治疗。
即便是现在,医生仍然需要通过针对病症来判断是否需要切除阑尾。所以也请千万不要怪罪割去你阑尾的那位医生,有些东西该舍弃的就舍弃了吧。
投稿邮箱:jiujiukejiwang@163.com 详情访问99科技网:http://www.fun99.cn